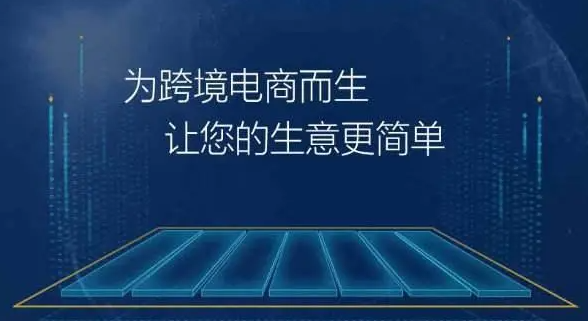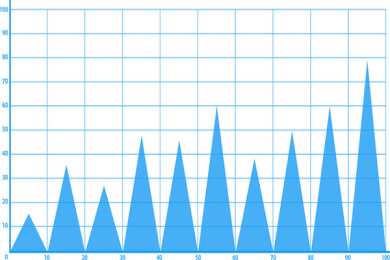少年将军误闯翠红楼,宁可打地铺也不碰我。后来却食髓知味
 admin 2025-04-26
74
admin 2025-04-26
74
《将军失信》
少年将军误闯翠红楼,宁可打地铺也不碰我。
后来却食髓知味。
他说要带我走却食言那日,花魁连骂他两个时辰都不带喘气的,而我倚窗摩挲着他的贴身玉佩,眉眼悠远。
一诺千金。
将军乃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岂会失信于小女子?
1
花魁叫白露。
花楼女子不想着为自己赎身,偏偏热衷于捡落魄书生,送银子送关怀,嘘寒问暖无微不至,还说日行一善是积大德。
可她捡的五十七个书生无一人高中,也没有人再回翠红楼报答她的大恩。
柳妈妈说她脑子被驴踢了。
整个西南府的花楼姑娘,就没有不笑她的。
我除外。
我只会给她买话本子。
有说千金小姐被落魄书生骗财骗身的,有讲花魁娘子被负心郎害得失心失财的,她看完吓得缩到我怀里,「那我没财,是不是就不会被骗了?」
我怎就没发现她如此机灵?
后来她但凡有十两银子,就要放九两在我这里。
她还笑出两个梨涡儿。
「你脑子好,你管钱我放心。」
我:……
肯听话也是好姑娘。
「寒露,咱们要做一辈子姐妹呀。」
冬天下雪的时候,她喜欢钻我的被窝搂着我睡,嘀嘀咕咕说些无趣至极偏又让人心头发酸的话。
我通常装睡。
听着她逐渐均匀的呼吸声,复又伸手将她揽进怀里。
一辈子那么长。
傻姑娘,别轻易许诺。
2
白露捡的第五十八个书生有些奇怪。
会静静的听白露说话,会把晾温的茶递到她手上,也会跟着她去后巷施粥,分给那些可怜的小乞儿。
乞儿里就数石柱最机灵。
他知道帮忙抬施粥的桌子,会叫乞儿们把吃过的碗洗干净,会乖巧的喊我和白露姐姐,也时常缠着赵秉玉教他写字,他学会了就教给其他乞儿。
赵秉玉总是不厌其烦。
我和白露说,他倒是个有耐心的,不像从前那些书生,满嘴酸话故作清高,见到乞儿们了只会皱眉头。
白露就抿着唇高兴的笑。
柳妈妈埋怨说,后巷都成了乞丐窝。
怪只怪这几年收成不好,百姓遭难,而她嘴上不饶人,私下却添了银子熬稠粥,还不肯叫人知道。
翠红楼的生意并不好。
西南府花楼多,那些姑娘又俏又媚还会花活儿,而翠红楼久居深巷姑娘们也随性自在,生意自然不如其他花楼。
所以柳妈妈叫我拢着钱九州的心。
钱家是西南府赫赫有名的富商,钱九州是钱家的独苗苗,去年他来了回翠红楼,我只陪着小坐会儿,指缝里漏出来的银子就够翠红楼上下吃用很久。
但花楼姑娘们对他又爱又恨。
无他,爱玩弄女子。
但初雪那日,他竟然来了。
彼时我正在白露房里看赵秉玉抄书,他一手隶书写的尤为流畅利落,引得白露满面羞意,挽袖为他磨墨。
而他抄书得来的银钱,也全交给了白露。
白露跟我说时,话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,想像着赵秉玉高中之后的风光景象,那些曾经震慑过她的话本子,好像突然就失去了效用。
我想劝她清醒。
但赵秉玉却坦荡磊落,叫我挑不出错。
他是第五十八个书生。
也许,他的确不同于旁人。
3
我下楼时,钱九州正赔着笑和一名年轻男子说话。
男子眉眼锋利,带着肃杀之意,身形宛若松柏挺拔昂扬,明明只有他一人,却像是有千军万马呼啸而来。
我心下微凛。
「寒露,叫宁爷。」
钱九州对上我时便敛了笑,眉目阴沉眼神如隼,我刚笑脸唤人,身后却忽然响起娇甜声音,「钱公子,寒露她不解风情,不如奴作陪?」
白露轻盈下楼。
明明她方才还在磨墨。
「白露!」
我低喝,她却朝我眨眨眼,暗中捏了下我的手又松开,明明是朵小娇花却固执的挡在了我身前,「西南府的姑娘们会的东西,白露都会。」
她撒谎。
翠红楼上下都对那些无底线取悦男子的手段嗤之以鼻,每回提起来她都要愤愤骂几句,何时学过那些手段?
「走开。」
我冷脸将她推到旁边,「没听见钱公子叫我侍候?」
她委屈巴巴的。
钱九州要笑不笑的扫了眼我俩,「两花争春,倒是有趣。只可惜像她那样的货色,西南府数之不尽,寒露,你可懂?」
「寒露明白。」
花楼女子大多娇媚可人,但今晚的贵客不喜这一类。
「两位爷,楼上请。」
柳妈妈适时插话,满脸堆笑的将人往我房里引,我落在后面瞪白露,「谁让你强出头的?也不怕赵秉玉多想。」
「我为我姐妹出头,干他何事?再说我本就是花楼女子,他若嫌弃,尽管离开便是。」
白露眼里蓄了泪,难掩担忧,「钱九州虽然阔绰,但西南府的姑娘们都知道他喜玩弄女子,我就是怕你会受折辱。」
这傻姑娘。
她怕我受折辱,难道她自己就受得住?
况且她对赵秉玉一片痴心,赵秉玉也对她爱护有加,虽说未来之事不可预料,但也许他们能修成正果呢?
我把白露赶回了她房间里。
刚到我门口,迎面碰上柳妈妈出来,她把我拉到一旁,说只要那位宁爷满意,钱九州愿意给这个数。
她伸出根手指。
我点头,「一千两是很大方了。」
「傻不傻?一万两!」
柳妈妈激动得两眼放光,「有了这笔银子,咱们冬日里就能用好炭了,各个房间也能添几床暖和被子,还有桌椅架子都得换新……」
要花银子的地方实在太多,她掰着手指头都算不过来。
我皱眉,「这等好事怎会轮到咱们?」
「那位爷挑的很。」
「钱公子带他去万花楼,但人家连凝香姑娘都没看上眼,花活儿才上那位爷就黑脸走人,钱公子也是不得已才找到咱们这里来。」
万花楼背靠官府,是西南府最好的花楼。
凝香姑娘则是万花楼的头牌,西南名妓,生得花容月貌又多才多艺,平日只见达官显贵,没想到却入不眼这位宁爷的眼。
柳妈妈双手合十,眼巴巴的看着我,「寒露,一万两啊。」
「我是谁?凝香又是谁?」
「妈妈您太看得起我。」
谁都喜欢银子,但那一万两也不是谁都能赚的。
柳妈妈却不服气,「你若愿意曲意逢迎,西南府能有她凝香什么事儿?再说反正凝香都没有拿下,咱就权当试试。」
柳妈妈时常说我不愧叫寒露,说我性情冷淡不喜迎合,生在寻常人家也无所谓,但在迎来送往的花楼里,我就是再美再多才,这脾气也足够让那些寻欢作乐的男人失去兴致。
我并不解释,乐得清静。
今晚不是钱九州点名要我,她也不敢叫我侍候贵客。
4
钱九州在和那位宁爷说话。
也不知对方什么来头,钱九州不见往日的乖戾嚣张,言语间透着小心翼翼的讨好,时不时还赔个笑。
「爷是军中的人?」
我落座,给那位宁爷倒酒,他既然不喜欢花活儿,那就喝喝酒聊聊天,也能省我的事。
他端酒杯的手一顿,眼神骤然凌厉,「你如何知晓的?」
「您身上,有金戈铁马的气息。」
我轻轻碰了下他的酒杯,温声说道:「不管您是谁,保家卫国都辛苦了,寒露敬您一杯。」
他这才缓了脸色。
对面的钱九州也舒了口气,递我一个警告眼神。
我当没看见,岔开话题问些军中的趣事儿,他倒也能跟我说几句,而后又道:「你倒是胆大,寻常女子莫说跟我闲聊,就是与我对视都不敢。」
「那是她们胆怯,与寒露何干?」
我做事论心不论人,没的随意怕过谁,而他盯着我看了两秒,忽就抿出点笑意来,「倒是有趣。」
他眉眼略弯,柔和了那股肃杀之意。
竟也是清朗如月。
「我就说,寒露姑娘与众不同。」
钱九州也笑起来。
见宁爷没有走人的意思,他便找借口离开了。
进来送点心的柳妈妈眉开眼笑,悄声叫我好好侍候,想来钱九州没食言,银子给到位了。
我点头。
翠红楼本来就是做那等营生的,柳妈妈往日也对我多加照顾,若这位宁爷有需要,我自不会拿乔使小性子。
但他只叫我陪酒聊天弹曲儿。
酒越喝越多,他眼神却依然清明锐利,待亥时过后,有人翻窗跳进我房里,他一面叫我不要紧张,一面跟那人低声说着什么,我识趣的略略加大了琴声。
人走后,他歉意的说要留宿在我房里。
但他会打地铺。
「钱公子付足了银两,莫说睡地上,就是睡寒露也使得。」
我实话实说,他却倏然涨红了脸,又莫名生出些恼意来,「宁某还是很敬重姑娘的,姑娘何苦拿宁某开玩笑?」
他竟说我不自重?
那我偏要叫他知道,花楼女子是如何撩拨人的。
窗外寒风呼啸,房里暖香融融。
轻纱滑落,我仰头眼角含泪的看他,「寒露说的都是知心话,但爷宁可打地铺也不上榻,莫非是嫌弃寒露?」
「我、我没有。」
他慌忙摇头,铁血肃杀的男人竟也会手足无措。
「那爷为何不敢看寒露?」
我轻泣着,柔若无骨的攀附上昂扬挺拔的身躯。
「爷是大英雄,奴是小女子,爷在阵前杀敌受万民爱戴,奴若柳絮无枝可依,原也就是奴贪心,竟妄想能得爷眷顾……」
腰间骤然一紧,后头的话被他吞进了唇齿间。
毫无章法,偏又勇猛凶狠。
帐顶儿摇啊摇的。
浮浮沉沉间,他咬着牙说我是小妖精,肯定是他喝多了酒才会着我的道,可他遍布伤痕的精壮身子却不肯停歇半分,横冲直撞任由热汗滑落。
我软着身子由他撷取。
酒醉还有三分醒。
谁信他的嘴。
5
他说他叫许淮宁。
说他来西南府是办事的,没想过假戏真做,但却着了我的道。
我说我知道,毕竟他还是初次。
但他食髓知味,龙精虎猛的痴缠了我一夜,翌日晌午离开时,他叫我等他,「寒露,待事了之后我就接你走。」
「好啊。」
我有口无心的笑应,「多久我都等你。」
男人的誓言就像水中月镜中花,能听不能信,谁碰谁倒霉。
他留了块玉佩为凭。
质地清润,上刻「许」字。
东西是好东西,他走后,我就放在了妆奁最底层。
柳妈妈如今红光满面。
有银子就有底气,她开始修缮翠红楼,也给姑娘们添了好炭好物件,还给乞儿们做了新衣新鞋每餐发个白馒头,石柱那孩子会来事,领着乞儿们给她磕头道谢。
柳妈妈笑的都合不拢嘴。
又连声说钱是我挣来的,要谢该谢我。
我不喜这种让人牙酸的场合,石柱却是个认死理的,每回我去施粥,他能把板凳擦了又擦,把我当菩萨供着。
若是我哪日没去,他都能托人三遍问好。
柳妈妈还撤了我的牌子。
说钱九州给够了银子,往后我只需好好侍候他带来的人就行,我琢磨着若不是许淮宁难搞,钱九州也想不起我这号人,正好我落个清闲。
白露倒是眼泪汪汪的。
「那男人瞧着就凶神恶煞的,看把你折腾成什么样了。」
呃。
一回生二回熟,后来许淮宁的确没少磨我。
我莫名的脸热起来,叫她不要瞎揣测,但她指着我锁骨上的青紫红痕就差抱着我哭了,我赶忙岔开话题,「赵秉玉没有为难你吧?」
「他说他会尽快给我赎身。」
说到她的小情郎,她立马羞怯起来,还说赵秉玉又接了给人写信作画的活儿,等攒够进京赶考的银子后,余下的银钱就交给柳妈妈,也让柳妈妈撤了她的牌。
这倒是好。
往年捡的书生只会哭穷要银子,说有出息了就报答白露,但那么些赶考的,竟无一人回来找白露。
赵秉玉倒是实干家。
我原以为许淮宁不会再来,便喊白露给我暖床。
谁知他半夜跳窗进来,把白露惊的不轻,转眼又骂他太粗鲁,「看看寒露都叫你折腾成什么样了!」
威风凛凛的男儿被她说的面红耳赤,半点都不敢还嘴。
等白露走了,他趴在床边,可怜巴巴的求安慰,「她凶巴巴的骂我,你也不帮我说情。寒露,我好伤心。」
谁教他撒娇的呀。
卸去满身的肃杀冷厉,他柔软的像小狗崽,湿漉漉的眼睛里好像只有我,我没忍住,亲亲他的唇,「那你今晚温柔些。」
他瞬间亮了眼睛。
献宝似的从怀里拿出捂着的烤红薯喂我,「闻着很香,就买给你了。」
不是值钱东西。
但却香甜软糯的过分。
他夜夜都来,除了那股横冲直撞的劲儿控制不住,有时会给我带吃食,有时是漂亮首饰,有时他会将我抱在膝上,细细亲吻我的眼睛。
「清泠泠的,宛若霜雪。」
他很爱这双眼。
最喜在情动时看着我的眼睛,一遍遍的唤我名字,既不能将我揉进他的骨血里,便要看着我为他失控,为他彻底沉沦。
偶尔他也会犯浑,问我心中可有他。
「当然有。」
他贪恋我的身子,我亦喜欢他的健壮,他夜半来黎明走,行事神秘为人谨慎,我也规矩的不多问半个字。
但他却埋在我颈间轻喃,「我能感觉到,你并不在意我的去留。」
傻不傻。
我吻住他的唇。
「只要你来,我就很高兴了。」
他若走。
那也是命中无缘。
6
人前的许淮宁依然沉稳凌厉。
有几回他和钱九州城还有一大帮公子哥儿来翠红楼,钱九州喊我陪他,他除了不赶我走,面色平淡的好似夜晚疯狂的人并不是他。
我也闭口不提那些事。
但钱九州很在意。
他反复问我许淮宁待我如何,且让我一定要哄住许淮宁的心,「只要能让他对你言听计从,我保你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」
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。
但想来不是好事。
「您看宁爷会是被儿女情长耽搁的人?他那夜是在我房中过夜不假,但过后就没再来了。」
我摇摇头,「您还是另请高明吧。」
他脸色阴沉未置可否。
晚上我跟许淮宁说起这事,他探入衣摆的手掌骤然顿住,眼中涌起寒芒,「钱家不安分,你做的很对。」
他没有细说,我也不追问。
只不过钱九州并不死心,时常带着许淮宁来翠红楼,有时许淮宁容我坐他身边片刻,有时就叫我滚,吐出来的话更是凉薄无情。
「妓子而已,也想翻天。」
晚上他负荆请罪。
双手捧着鞭子乖乖的举过头顶,「请娘子责罚。」
「别乱叫。」
我佯怒瞪他,看他低眉顺眼的讨饶样儿又舍不得多说重话。
他倒是极有眼色的贴上来,把我往怀里带,「不叫娘子叫什么?是为夫的错,罚为夫今晚好好侍奉娘子。」
我:「……」
他敢不敢再罚的重点儿?
7
许淮宁演的很好。
钱九州大抵是信了他对我的不在意,逐渐也不来翠红楼了。
但大雪过后,许淮宁却忙起来了。
时常几天不露面,有时来了还没喝上热茶就有人找他,那些人个个身手矫健目露精光,想来也是军中的人。
不知他们在商量些什么,但有回来找他的人拔高了声音,「将军让您尽快回去!」
许淮宁下意识的望向我这边。
我望着窗外。
落在我身上的视线没多久便移开了,也许事情紧要,那夜他留下一句「等我」便跟着他们走了,直到年三十也没有回来。
白露和赵秉玉陪我吃年夜饭,赵秉玉还画了一幅雪夜嬉戏图送给我,说感谢我经年来护着白露的恩情。
我嗤他,「我与白露多年姐妹,岂用你来谢?」
但我把画挂在了房里。
白雪皑皑红梅吐香,画中姑娘闲坐廊下饮酒,笑看不远处踮脚嗅梅香的娇憨少女,夜雪籁簌风灯暖黄,端的是宁静雅致,悠然自在。
甚得我心。
我和白露闲暇时也会帮赵秉玉抄书。
他是个很有想法的人,说当今朝廷权臣当道吏冶紊乱,说西南府原是农粮重要产出地,却不兴农耕管理无方,说他若入朝为官必将促使新政推行,还说民以食为天,国以民为本,只有百姓富足,国家才能富强。
我深表赞同。
抬眼一看白露,满脸都是与有荣焉的高兴样。
她都不知如何欢喜才好了。
年初八,夜半窗动。
今夜落了春雪,许淮宁带着寒气翻窗进来,玄衫已被浸湿,且脸色憔悴风尘仆仆,似赶了很远的路。
「寒露。」
他等不及烘暖身子,便疾步将我拥入怀里。
又似怕冻着我,敞开外衫让我靠在他胸膛上,我却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,心头骤然一紧,「你受伤了?」
「嗯,一点小伤而已。」
他浑不在意,低头寻到我的唇,这才满足的喟叹了声。
良久,他才松开我,轻轻拢好我散乱的鬓发,「我只能待半个时辰,且这几天可能会有动乱,你乖些,莫乱跑。」
这人拿我当孩子呢。
明明是他更呆憨。
明知只有短短的半个时辰,却依然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奔赴而来,只为那片刻的相拥。
我忍着酸涩,给他沏了热茶又换掉外衫,端来一盆热水给他泡脚,他却急忙避开了,「哪能让你给我洗脚?」
「你心里有我,你便值得。」
雪夜寒凉,他身上有伤还来去匆匆,泡脚能让身子暖和些,也解解疲乏。
他脚上都是陈年旧伤。
我到底没忍住,「这回又是做什么伤的?伤哪儿了?」
「蛮贼狡猾,但我把他们打退了。」
「喏,伤在这里。」
他还挺骄傲的撩起衣摆给我看腹部的伤,白纱布缠了好几圈,看不清伤成什么样了,但想来没他说的那么轻松。
「别哭呀。」
他一下慌乱起来,粗砺指肚小心翼翼的抹过我眼角,「我被那蛮贼捅刀子的时候都没觉得有多疼,你一哭,我这心倒像是要碎掉了。」
「是心疼你,敬重你。」
我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,但他的确给了我很大震撼。
究竟是多虔诚的信念,才会让他愿意抛头颅洒热血,以凡人之躯替百姓筑起一道道坚固的屏障?
「你懂我,我便也值得。」
他的吻柔情似水。
眷恋的在我唇上辗转流连,「眼下边关不太平,等战事了了,我带你看大漠落日,鹰击长空,看将士们浴血奋战守下来的壮丽山河。」
不是甜言蜜语。
却听的我心头呯呯乱跳起来。
那是他的世界,是我不曾见过的天地,若有那一日,我定当慷慨赴约。
8
许淮宁走了。
我不知他回了边关,还是在西南府。
我约白露去白马寺上香,她眨巴着眼,满脸奇怪的打量我,「你不是从来都不信鬼神?怎地突然转了性子?」
我被她看的脸上发烫,作势要挠她痒痒。
她笑着讨饶,到底是陪我上了趟白马寺,我把求来的平安符和玉佩放在一起,但直到上元节那天,许淮宁也没再来过。
钱家却出了大事。
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滔天大罪,一夜之间钱家上下通通被打入死牢,听说官兵上门时钱家不止负隅顽抗还打死了人,惹得知府老爷大怒,连钱家的狗都没放过。
柳妈妈吓白了脸。
叫小乞儿们去打听情况,却只知钱家通敌叛国,钱家上下不日即将斩首,倒也没提钱九州和花楼里的瓜葛。
我倒是担心那个被打死的。
私下给了石柱银子,让他去打听清楚,也只得知钱家被抓当晚确实死伤了不少人,但具体情况连官差都说不明白,除非去问知府老爷。
我思前想后,拿出了那块玉佩。
但没等我想好如何找知府老爷打听许淮宁的情况,夜里就有一支利箭带着信射进我房里,信中有两行字,还附了千两银票。
「千金抵一诺。」
「你我断前缘。」
白露就在我房里,我还没怎么着,她先哇哇哭起来。
直骂许淮宁是负心汉。
即将进京赶考的赵秉玉轻声哄她,回头又跟我说:「燕朝有位许靖国大将军,那人也姓许,你若想打听,我进京之后帮你查个清楚。」
「不了。」
我摇头,谢绝了他的好意。
许淮宁是什么样的人,我心里清清楚楚,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背信弃义。
想必是有不得已。
我既帮不上忙,那就不添乱。
9
两日后,赵秉玉进京了。
他去年中举,今年要赶春闱,若是能鱼跃龙门,以他的性子想必不会负了白露的一番情意。
情郎走了,白露也丢了魂儿。
我说今年想酿桃花酒,她说梨花还没开,我说拿胭脂,她给我递梳子,有回半夜还冲进我房里抱着我哭,「寒露,我梦见玉郎浑身是血的叫我救他,我好怕他会出事!」
「他是进京赶考,不是上阵杀敌。」
她伏在我怀里哭。
而我下意识的,按住了挂在心口上的玉佩。
上阵杀敌的那人,也要平平安安的。
十日后,钱家人于菜市口斩首。
我和白露远远看着,唏嘘世事无常,谁知道钱家竟敢通敌叛国?想来许淮宁也是为了彻查此事才来的西南府。
「午时到!」
法场上响起雄浑声音,我捂住白露的眼睛,怕喷溅的鲜血吓到她,但刽子手刚扬起刀,远处忽有无数的马蹄声飞速赶来。
刚接近,大片的箭雨就凌空掠过,射倒了维持秩序的官差,也射倒了大片百姓。
「有人劫法场!」
惊怒声如炸雷般响在菜市口,百姓们四散奔逃,我也立即拉着白露躲进了旁边的馄饨铺,而那些劫匪如狂风般冲向法场,很快就砍倒了前来阻拦的官差们。
钱九州得了救。
众目睽睽下,他一刀砍在负责监刑的知府老爷身上,「听说你为了让许靖国那个老匹夫消气,把我家的狗都杖杀了?」
知府老爷的惨叫声让人头皮发麻。
我心头狂跳。
许淮宁身份不低,而他又和许大将军同姓,眼下钱九州说知府老爷想让许大将军消气,该不会是那夜许淮宁在钱府……
不会的。
不会的。
我极力保持冷静,就听钱九州在法场上高喊。
「各位父老乡亲听着!皇帝老儿昏庸无能,这个狗官为虎作伥,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来抢我钱家百年基业,今儿我钱家在此反了!」
「敢和我作对,这就是下场!」
声未落,鲜血骤然喷溅而起。
曾经被赵秉玉说不作为的知府老爷,当众被钱九州砍了头。
无人敢出声。
钱九州大摇大摆的出了法场,那些高鼻梁深眼窝的黑衣人跟在他身后,若说他没有通敌,谁都不信。
可谁敢在这时候触霉头?
「不好!」
我看着钱九州离开的方向,忽然反应过来。
他怕是要去翠红楼!
10
许淮宁在西南府时只亲近过我。
钱九州恨毒了他,怕是不会放过与他有关的任何人。
「怎么办?」
白露急的直哭,眼巴巴的看着我,我稳住心神,立即找馄饨铺的老板换了两身旧衣服,「先出城。」
钱九州是突然发难的。
就算他能夺下城门的掌控权也需要一定时间,先趁乱离开再说。
我和白露换了男装。
远远的从翠红楼那边绕过去,果见有黑衣人守在门口,而城门口杀声震天,大批训练有素的黑衣人正在剿杀守城军,我和白露混在拼命奔逃的百姓中才跑出城。
刚跑没多远,回头就见城墙上的旗帜被一刀砍断。
有人在城楼上高喊。
「关城门!」
厚重城门缓缓降落,发出吱呀声响。
我眉心一跳。
迟半步,我就是瓮中的鳖。
城里城外哭声震天,还有人试图拍打城门,眼看大批黑衣人挽弓站上墙垛,我没迟疑,立即拉着白露不要命的往前狂奔。
身后响起利箭的破空声。
只不过刹那,哭喊声就成了惨叫声。
宛若人间炼狱。
「嘶!」
我手上骤然一沉,白露踉跄着扑出去,我一低眼就看见了她后背上的长箭,箭羽还在微微颤动。
「白露!」
「快走,你快走……」
她连声催促,都忘了叫疼,我红着眼背起她,只管往前跑,「说好做一辈子的姐妹,少一天都不算!」
颈窝一片濡湿,我没敢回头看。
钱九州竟然屠杀平民。
畜生!
11
西南山多路崎,天堑林立。
我并非土生土长的西南人,来西南府后也终日在翠红楼,很少外出,我背着白露顺路跑时石柱冒出来拦住我,将我们带到了李家村。
村里只有个赤脚郎中。
看着背上中箭不时咳血的白露,他头摇的像拨浪鼓,「就算我敢给她拔箭,村里也没有她要用的药草。」
「先拔,有什么药就上什么药。」
我紧紧握着白露的手。
她咳了一路的血,手已经泛凉了,曾经笑起来弯弯如月牙儿的眼睛紧闭着,就算我给她呵手,她也不肯睁开眼看看我。
她骗我。
她也想毁约是不是?
「李爷爷,城门关了,谁都不准进出,您就救救白露姐姐吧……」
石柱抹着泪哭,他也是趁乱出的城。
他知道我和白露去法场看行刑了,在见到钱九州带人守住翠红楼的时候就第一时间跑出了城,守在岔路上等我和白露。
我问他,就不怕我和白露并不会出城吗,他还摇头,「姐姐你那样聪明,肯定会先出城然后再想办法。」
他倒是心思灵巧。
「拔,死了不怨您,活了我给您立长生牌。」
李老爷子还在犹豫,而我看着呼吸越来越微弱的白露,拿起剪刀几下剪开她背上的衣服,露出已经发红泛紫的皮肉,「您不敢拔,我来,您给她上药就行。」
箭在右肩胛下,入体约有两寸。
待药备好,我又给白露嘴里塞了块布,沉下心,握住箭杆的右手猛然用力。
「按住了!」
鲜血一下飙起半丈高,溅了我满头满脸,昏迷中的白露也剧烈抽搐起来,石柱死死按住她,而等候的李老爷子也连忙上前给白露洒上药粉。
药粉洒上就被血冲走了。
老爷子急的额头上冒汗,而我抓起他备用的草药把药粉洒上去,然后将草药按在伤口上,白露疼的闷哼,而我眼也未眨,一错不错的按着。
半晌,血流终于缓了下来。
「这娃娃,狠着呢。」
石柱家只有个年迈多病的奶奶,李老爷子跟她在外头说话,刚巧石柱掀开几块破布拼成的帘子,端了水进来给我洗脸,我问他,「老爷子说我狠,你怕不怕?」
「不怕。」
他摇摇头,满眼崇拜,「拔箭是死,不拔箭也是死,那不如拔了箭图个生机。姐姐你果断坚决,是做大事的人。」
「你还夸我。」
半大孩子聪明的很,知道是非好歹。
只是……
我眉眼低垂浮起冷意,很久以前也有人笑呵呵的将我抱在膝上,这样夸过我,只可惜人间事不讲人间理。
不知造就了多少屈死冤魂。
我随身带着银票,拿给石柱去药堂给白露买些药回来,再打听下翠红楼的情况,但他很快就沮丧的回来了。
「城门没开。」
西南多天险,府城更是依山而建,城门一关,易守难攻,钱九州想必也是看中了这一点,才夺城占地。
李老爷子的草药很简陋,当天晚上白露就发起了高热,我迷迷瞪瞪的看见柳妈妈浑身是血的哭喊,猛的惊醒过来,就见石柱奶奶在给白露换帕子。
「你才刚眯着,多歇会儿。」
老人家笑的很慈祥,「你别听李老头嚼舌根。他自己胆子比粟米还小,却说你手狠,怨不得他一辈子只能做个赤脚郎中。」
「谢谢您。」
我没想到石柱奶奶会帮我说话。
她叫我再睡会儿,但我想着梦里柳妈妈的惨状,怎么也睡不着了,眼看天将黎明,索性叫上石柱往城里赶。
城门还关着。
我连蹲三天,三天城门都没开。
白露高热未退,烧的满嘴胡话,一会儿哭着喊我快走,一会儿又玉郎玉郎的叫,我担心她的伤又着急翠红楼的情况,急的起了满嘴燎泡。
思来想去,我叫来了石柱。
让他给我递封信。
12
早春的夜晚依然寒凉。
我摘了枝刚吐嫩芽儿的柳条,赶着小马驹踢踢达达的到了城外空地上,刚站定,就听城门吱呀响起来,大片火把蜿蜒而出。
钱九州被人群簇拥着,摇曳的火光照在他脸上,更显阴森狠戾。
「寒露,本王更欣赏你了。」
他站在城墙脚下朝我喊话,声音随着夜风远远荡开。
「枉我在翠红楼守你,你却狠心溜走了。眼下单枪匹马的来见本王,可否是想明白,要归顺本王了?」
「你竟自封为王?」
我不答反问,而他笑容自得,「我现在可是平西王!」
「寒露,他许淮宁有什么好的?眼下战事四起,他自顾不暇,皇帝老儿又只会饮酒作乐,你及早依附于我才是上策!」
呸。
皇帝的昏庸我不是今日才知晓。
但他通敌叛国,人人得而诛之,也敢厚颜无耻的标榜自己才是正义之士?
「我来是想告诉你两件事。」
「第一,我与许淮宁只有露水情缘,你抓我泄愤又或是用我威逼他,都没有意义;第二,我人在城外,你为难翠红楼的老鸨和姑娘们,只会显得你更心胸狭隘,毫无男子气概。」
「你!」
他骤然生怒,我轻呵,「钱九州,你可真让我看不起。」
什么平西王,只是个屠城的畜生而已。
他脸色彻底阴沉下来,过不久,忽又朝我笑道:「既然你说和许淮宁没有情意,那你进城,只要你在西南府,我保证不动翠红楼的人。」
「你当我傻?」
我嗤声反问,「你会因为一句话,而把性命送给别人掌控?」
他脸一沉,黑如锅底。
「该说的我都说了,其余的你随意。毕竟你是平西王,你才是以后要掌管这片土地的人,你的百姓轮不到我操心。」
不是想占城吗。
狡诈如他,自然懂得民心才是根本。
我骑马转身,柳条一抽,小马驹瞬间撒开四蹄,飞奔进夜色里。
身后传来怒不可遏的大叫声。
「寒露你给我停下!」
「追!」
13
月色溶溶,风凉如水。
马蹄声遥摇传来,钱九州的人仍咬着我不放。
我一路跑到十里亭,石柱牵着匹同样矮小但精壮的马匹在等着,见我来,他立即上马启程,「姐姐,我走啦!」
「按计划行事!」
我只得来得及喊一句,他已经跑远了。
那是匹壮年马,比我这匹小马驹的脚程快多了,而我牵着马躲进旁边的山林里,不多时,一大群黑衣人举着火把骑着马赶到十里亭,又呼啸而过。
我把马赶进深山,然后返回城外的小山坡上。
钱九州还在。
月渐西沉,黎明时他才走。
也许是他想通了,又或是有人劝他,城门如我所设想的并没有再关上,而追我的那批黑衣人也没有回来。
石柱会把他们引往百里外的荣宁县,那里四通八达,他弃了马再光明正大的从荣宁县回来,而我则换成男装混在焦急进城的百姓里,杀个回马枪。
只不过三日,便恍如隔世。
从前的西南府,黎明时就有挑菜赶鸡的百姓进城,小面摊的汤锅里也咕嘟嘟的冒着诱人香气,若是日光晴好,小摊贩们的吆喝声能像夏天的蝉,没完没了。
如今却满街狼藉。
街边店面大多都紧闭着门,偶有几个行人也是神色匆匆,唯独我的画像满城可见,贴遍了大街小巷。
钱九州为了找到我,怕是把整个西南府城都翻了个底朝天。
我转了几条街,才给白露买到药。
绕到翠红楼,大门口依然有黑衣人守着,后巷倒是安安静静的,曾经的小乞儿们都不见踪影了,我正想着怎么混进去,楼上却忽然吱呀一声响。
柳妈妈神情痛苦的呆站在窗边,有风吹过,她的左袖竟然随风飘起。
我死死捂住了嘴。
眼泪不受控制的急速飙出来,模糊了窗前的人影,钱九州抓不到我,竟然伤害柳妈妈!
「咳!咳咳!」
楼上忽然响起咳嗽声,我抬头就对上了柳妈妈惊喜又焦急的眼,她小幅度的快速摇头,无声的叫我快走。
她背后有雄浑声音传出来,「有人?」
我迅速贴在了墙根下。
就听柳妈妈带着哭腔在求饶,「我疼的厉害,爷,给我找个好大夫吧……」
房里充斥着骂声。
等声音远去,再抬头,柳妈妈已经不在后窗。
我咬着牙飞快的跑出后巷,一路奔回李家村,白露浑身滚烫,都翻白眼了。
石柱奶奶熬好药给她撬开嘴灌下去,她都不怎么吞咽,李老爷子在旁边直摇头,「怕是不成了,准备后事吧。」
「闭嘴吧你。」
石柱奶奶骂他乌鸦嘴,又叫我放宽心,但我心里像烧了把火,烧的我眼珠子赤痛发红。
白露重伤。
柳妈妈断了左臂。
翠红楼其他姑娘还不知是何情况。
都是钱九州害的。
都是他!
眼见灌下去的汤药又流出来,我端过药碗喝了一口,随即捏住白露的鼻子,覆唇将药渡过去。
身后的老头儿惊叫,「成何体统!」
我置若罔闻。
石柱奶奶撵走了他。
渡过去的药又流回来,我又再渡,反反复复,一碗药她终是咽下去大半。
下半夜,高热终于退下去了。
「谢天谢地。」
石柱奶奶抹着泪磕头感谢菩萨,我张张嘴又终究没说什么,白露仍在昏迷中,我打了盆水,仔细的给她擦身子。
当初我在大雨中倒在翠红楼后巷的时候,是白露把我从泥泞中扶起来,她眨着圆圆的眼睛,笑着说让我别害怕,她会照顾我直到好起来的。
后来她真做到了。
她说,我叫白露,你叫寒露好不好?
她说,你要多笑呀,笑起来更好看。
她把难缠的恩客揽过去,把她辛苦挣来的银子全数拿给我,她在冬夜里抱着我说要做一辈子的姐妹。
她却忘了我这人不讲理。
她说过的话就不准食言。
14
我把白露托付给了石柱奶奶。
又只身回城。
柳妈妈和其他姑娘还在翠红楼受苦,我不能放任不管。
城门口还张贴着我的画像,守城的士兵也换成了那些高鼻梁深眼窝的黑衣人,但我搽丑了脸又是男装,并没有人注意到我。
「紧急集合!」
我刚转到翠红楼对面的小巷子里,就见长街上有人骑着快马传令,很快大批的黑衣人不知从哪冒出来的,又聚在一起,纷纷涌向城外。
我看的心惊。
他们的相貌与关外蛮贼无异。
我只以为钱九州想借助外力霸占西南,然后起兵造反,可眼下却有大批蛮贼跟随他出现在西南腹地,是想做什么?
「贱妇!」
翠红楼门口忽然响起斥骂声,一群黑衣人押着柳妈妈和姑娘们出来,而钱九州阴沉着脸疾步前行,「人跟丢了,那就把她们押到城中心祭旗!」
他走的极快,似火烧眉毛。
该是石柱成功了。
而柳妈妈和姑娘们像是刚受过刑,浑身是血的被黑衣人拖向城门口,我混在人群里想要设法搭救,柳妈妈却似有感应,隔着人群望向了我。
「跑啊。」
她无声的张着嘴,似乎想朝我笑一笑,鲜血却大股涌出,染红了我的眼。
我不肯,双眼通红的跟着人群。
「姑娘们,唱个曲儿吧。」
柳妈妈忽然出声,沾了血的脸上满是笑容,她抬头望着瓦蓝天空,轻声哼唱起来。
「姑娘你往前走,」
「莫回头……」
人群中哭声渐大,被蛮贼驱赶到中心广场的百姓都如我一样红了眼眶,泪流满面,而我曾经的姐妹,那些可爱的姑娘们却都扬起笑容,跟着柳妈妈轻轻唱起来。
「你往前走,莫回头,
「你是马儿就要快快的跑,」
「你往前走,莫回头,」
「你是鸟儿就该高高的飞。」
「……」
我懂了,我懂了。
看着广场上集结的数百蛮贼,我明白钱九州为何非要抓住我了。
他并非是利用我报复许淮宁。
他是怕我向许淮宁通风报信!
他勾结外敌以雷霆之势侵占西南府城,不是想占城为王,是要以此为据点,和关外蛮贼里应外合,打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一个措手不及!
若被他得逞,边关被蛮贼踏破时,也就是百姓水深火热之际!
那时哪还有什么大漠落日,壮丽山河!
唇被咬破,嘴里弥漫起浓郁的血腥味,我噙泪看着被拖到广场上的柳妈妈和姑娘们,脚下却是一步步往后退。
又猛地转身,奔进了巷子深处。
风里马蹄声疾,隐隐传来腔调怪异的西域话。
「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」
「杀!」
我下意识的回头,就见蓝色天空下飞过数不清的光影,像是早春落下的一场寒雨,冰冷盛大,夺人性命。
我扶墙干呕了几声,又在漫天惨叫声中踉跄奔跑。
蛮贼都聚到中心广场去了,我奔到另一条街的威武镖局想找匹快马,不想镖师们躲在暗处都还活着。
「无需酬金。」
「我虽不如好汉你英勇,但愿护送好汉一程。」
知道我想去西北边关报信,总镖头双目赤红,立即派了最熟悉路的镖师给我,而我和林镖师趁城门口无人值守,飞快的奔向远方。
蛮贼凶残。
休想践踏我燕朝河山!
15
林镖师对西南西北了如指掌。
我与他昼夜兼程,赶到陇西时已精疲力竭,再从陇西奔赴到阳关,我只来得及把那块玉佩交给守城士兵便晕了过去。
朦胧间,烛火如豆。
日思夜想的那人一身银白盔甲,粗砺指肚轻轻抚过我的脸,「寒露,别等我了。」
「许淮宁!」
我猛地坐起,泪痕未干。
一座陈设简单的帐篷映入眼帘,而帐外响过整齐划一的脚步声,我跌跌撞撞的奔到外面,月光下,就见许淮宁身骑战马,正准备领队出征。
「你站住!」
我顾不得那些诧异眼光,踉跄着向他跑过去,哪知身子太过虚软,竟然一头栽下去,正准备跌个跟头,余光里却有人影闪过,将我捞入怀中。
「寒露……」
轻浅叹息响在耳畔,他低头看我,眼神复杂。
「不必解释,也不用愧疚。」
「蛮贼猖狂毁我河山,你自有更重要的事去做。若能事了,你别忘了那夜之约就成。」
我借着他的力站起来。
定定的望着那双明亮柔和的眼睛,「林镖师不如我清楚,你耽搁一刻钟,我把西南的情况讲给你听。」
战火四起山河破碎。
我欲与他话缠绵,可战场不是风花雪月的地方。
「你留在陇西等我。」
交待完,他紧紧拥我入怀,我闻到他身上浓郁的草药味,终究还是哽咽了,「上元节那夜,你受了重伤?」
「就知道瞒不过你。」
他叹息,而我把求来的那枚平安符挂在他腰上,随即后退半步,「白露还在西南,我就不留在陇西等你了。」
「你保护山河万民,便也是在保护我。」
「待边关事了,百姓安宁时,我定然赴你那夜之约。」
他不止是我的许淮宁。
他亦是百姓的守护神。
虽天涯海角,朝朝暮暮不相见,但从此心心相印永不疑他。
月光下的许淮宁威风凛凛。
唇上的吻又狠又重。
也不过两个呼吸间他便放开了我,深深的盯着我看了几秒,随即翻身上马,振臂高喝。
「出发!」
16
我连夜叫上林镖师回西南。
他不解,「西北有许将军父子镇守,相对平安,你还回西南干什么?」
「因为西南也有很重要的人在等我。」
我走时白露还在昏迷中,什么都不知情。
我怕她醒了会着急。
经过一线天时,远远听见前面有喊打喊杀声,我和林镖师爬上高坡眺望,黑白双方正在激战。
「咱们只快半天脚程。」
林镖师捏了把汗,「若不是李兄你赶在蛮贼出发前便赶往边关,那只怕,只怕会……」
「血流成河,生灵涂炭。」
我说了他想说都没敢说出来的话。
若后方被偷袭,就算是有许家两位将军镇守,也要死伤遍地。
而此时许淮宁提前赶到一线天埋伏,蛮贼被瓮中捉鳖,也算是提前化解了钱九州的阴谋。
一线天,钱九州满眼血红。
边打边往后撤,嘴里还在疯狂的叫骂,「许淮宁,是寒露那个贱人给你通风报信对不对?老子就知道她会坏事!」
「你也配提她的名讳?」
许淮宁挽弓搭箭,瞄准了人群中间的钱九州。
眼看一箭即中,钱九州却猛地将身边蛮贼拽过来挡箭,转眼又哈哈大笑的飞窜而去,「你赢了这回又如何,许淮宁,你抓得到我吗!」
高坡上春风料峭。
林镖师忧心忡忡,「李兄,钱九州溜了,咱们还要回西南吗?」
「他不会再回西南了。」
事情败露,他手底下的蛮贼又死伤过半,他只会像毒蛇般又缩回阴暗角落里,伺机再给许淮宁狠狠一口。
底下的将士在打扫战场,林镖师问我要不要去见许淮宁,我摇摇头,我并不擅长行军布阵,就没必要给他添乱了。
知他活着,便已足够。
李家村距离西南府城只二十里路,但山高路险,进出不易,也算安全。
白露已经醒了。
得知柳妈妈和众姐妹的惨况后,她连哭了几天,石柱和石柱奶奶也给众女立了牌位,「你们养活了石柱,老婆子都还没亲自去谢过你们,你们却……」
她佝偻着腰絮絮叨叨的。
我听的心酸。
花开花落,物是人非。
白露落下了病根,稍吹冷风就连天咳嗽,我叫石柱打听城里的情况,得知城里已经换了新知府,那群黑衣蛮贼也没再来过,这才带着白露进城看病。
大夫说她伤了肺,只能好生养着。
翠红楼已经荒了。
楼里陈设依旧,蒙了厚厚的灰,我和白露祭奠过众女,便又返回了李家村。
山中无岁月,但她常忧思重重。
我知她思念赵秉玉。
但石柱常去城里转悠,并没有打听到有关春闱的消息,且入夏后那群蛮贼竟又洗劫了西南府城,听说那位新来的知府都吓得连夜逃的不知去向。
西南似乎被朝廷遗忘了。
白露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,我将她揽进怀里,「入伏后,我们去京城。」
我不愿再踏足那处。
但她的情郎在那里。
17
白露吹不得冷风,所以入伏后才出发。
石柱想跟着,但石柱奶奶年迈多病,他只能留下来照顾,我给祖孙俩留了银子,便和白露出发了。
我依然找了林镖师护送。
从西南斜插西北,再北上京城,他熟悉路,能省很多时间。
白露还有些羞。
举着小铜镜左看右看,不是觉得颧骨比从前高了,就是觉得头发比从前少了,我说她,「再不好好吃饭,你能瘦到你的玉郎都认不出你来。」
她遭了大罪,又日夜思念情郎。
早就瘦脱了相。
她大概是把这话听进了心里,吃饭时就特别积极。
但到陇西,走不了了。
林镖师打听情况回来,脸色凝重,「钱九州狡猾,经常袭击陇西,许小将军领了一支兵追击他去了,如今都不知道双方打到了哪里。眼下阳关无主将,而玉门关外的匈奴又死咬着许大将军,他那边自顾不暇,阳关也岌岌可危。」
白露说道:「就没有援兵吗?」
- 上一篇:交付就挂10万/㎡?古翠隐秀真的这么好?
- 下一篇:萧山,一路跃升!一路出圈!
- 同类文章
- 友情链接
-